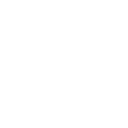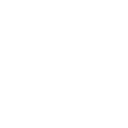平博体育规则,平博体育,平博真人,平博棋牌,平博彩票,平博电竞,平博百家乐,平博电子,平博游戏,平博体育官方网站,平博体育官网入口,平博体育网址,平博体育靠谱吗,平博体育app,平博app下载,平博投注,平博下注,平博官方网站,平博最新入口,平博体育平台推荐,平博体育平台赛事,平博赛事,平博在线体育博彩,平博足球博彩,平博足球投注,平博娱乐场

影片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以毕正明从卧底到归队的情节模式讲述了英雄正名的故事,以其突出的叙事风格带来了恣意酣畅的视觉体验。同时,这种风格的极端化又导致了空间层叠、主题失焦、节奏跌宕等问题,如同形成一个视效混杂的叙事漩涡。影片在空间设置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忽略了空间中人的真实性和立体感以及空间与外在环境的基本关联;正名之路的情节主线中掺杂了繁杂的副线,使得整个叙事链条失重,主题弱化;叙事节奏的随意和起伏不定虽然有新鲜感,但快节奏掺杂着信息密度与情感碎片,既无悬念也无留白,缺乏情绪沉淀的心理空间,导致影片的逻辑断层。
近年来,一些影视创作将故事背景锁定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距今不算遥远的年代,经历了经济改革、社会转折、城市变迁,很多人都切身体会过家庭悲喜和人世沧桑,这些独特的议题无不牵动着观众心理。借由这样的时代背景,创作者叩开观众的记忆之门、情感之门,构建主题各异的悬疑故事,呈现之间的明暗较量,进而探讨人性善恶、传递价值正念。近年来的网剧《树影迷宫》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胡同;此前引发热议的《漫长的季节》呈现的是90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厂区;《风吹半夏》讲述了那个变革年代的女性创业故事;《山海情》则聚焦90年代的大西北,讲述普通人建设新家园、脱贫致富的故事。
影片《毕正明的证明》以90年代为背景,讲述反扒警察毕正明的正名、正道之路,在时代氛围的营造、空间设置以及人物塑造上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看,封闭而流动的列车车厢是极限境遇叙事的典型空间,以题材影片为例,既能在正邪力量的智勇对战以及反转周旋中打造独特的视觉效果,也可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容纳复杂的世相人性,彰显艺术创作的人文思考。二十多年前的影片《天下无贼》即是在列车车厢的封闭空间中讲述天下有贼、贼中有道的故事。在川西塔公高原修庙的孤儿傻根带着五年的积蓄——六万块钱踏上返乡的列车,心怀盖房娶妻的平凡理想,于是在两队窃贼和便衣警察一行人之间展开守护与破坏的争战。当影片《毕正明的证明》亮相时,有着似曾相识之感——封闭的列车空间、伺机而动的偷窃团伙、良知被唤醒的盗贼,这些表层的视听元素非常相似,但是两部影片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毕正明的证明》在空间设置、主题表达、叙事节奏等方面彰显出更加个性化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吸睛的同时也容易让人迷失,因为一旦风格化的尺度没掌握好,就容易用力过猛、偏离主题,形成一种混杂失序的叙事漩涡。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市场化改革、时代的脉搏在现实中具体化为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陷阱,置身其中的人们被裹挟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中试探、前行,在欲望的漩涡中不断浮沉,兴奋、骚动、惶恐……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年代,也是不断被讲述的时代。正因此,很多影像作品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在这一社会经济转型、日常生活变动的时期,尤其是悬疑题材影片、网剧,在不同的地域风貌中构建各样的悬疑故事,呈现普通人在生存荆棘、精神创伤、极限境遇中的人性抉择以及复杂面向。
影片《毕正明的证明》对时代氛围的烘托主要体现在空间设置上。“任何叙事作品都必定会有一个或多个故事空间,因为构成故事的一系列事件必然会占有一定的空间,就像它们必然会占有一定的时间一样。”[1]封闭的列车车厢以及扒手聚集的日常生活空间,都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氛围。列车车厢作为封闭且流动的空间是故事发生的主场景,影片开始将近十五分钟都在铺陈火车站的外部环境以及车厢内部的空间特征。镜头从特写的列车时刻表、刺耳的火车汽笛声、清晰的车站广播,到熙攘的进站人群和候车厅局部场景,最终落在拥挤嘈杂的从哈尔滨开往广州的161次列车车厢里。这一系列快速切换的镜头辅以日常联络的通讯工具BP机、毕正明在母亲的服装店玩的游戏机等道具,营造出氛围感十足的时代背景。直到女主角“大白桃”的偷窃团队“横一队”现身,“秀”了各种偷窃技术,由此展开矛盾的主场景和爆发点,由北向南的列车上聚集了警察和好几个分属不同帮派的偷窃团伙,之间的斗智斗勇以及偷窃团伙之间的内斗就此展开。之后,偷金牌、铜镜等关键事件都是在车厢内发生,尤其是片尾毕正明和“花手”在车厢卫生间的打斗场景,在列车车厢这个整体封闭的“铁盒子”中将收尾环节的关键场景安排在一个更小的封闭空间中,在极限处境中逼出人物的情感流露,既是作为警察的毕正明对作为盗贼的“花手”的最终胜利,也是作为普通人的毕正明对曾经优秀的林乐华走上邪路的感慨和惋惜。此外,围绕车厢空间所延伸的铁轨、站前宾馆也是充满时代特征的空间设置。“花手”杀害铁路警察,与毕正明打斗、与少爷打斗都是发生在夜晚的铁轨旁,这样使得封闭的车厢和开放的铁轨形成车厢内外的呼应与对照,共同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空间呈现。
影片中的日常生活空间也承担着烘托时代氛围的重要作用。毕正明第一次跟着“大白桃”的偷窃团伙“识人”是在菜市场,从二楼俯瞰菜市场的全貌,蔬菜、海鲜、布匹,热闹又嘈杂,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息,挑野生江鱼且口袋放着红塔山的有钱男子、戴着随身听和假手表的墨镜男,还有和小男孩搭话的人贩子……这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十足的生活场景。片尾,反扒队集体出动逮捕英雄会成员的场景则设置在商业气息浓厚的银河商场,局促的走道、林立的柜台、时代感浓厚的服装,固定在墙上的插卡公用电话,以及堆满货物箱和蛇皮袋的过道、闭合的卷闸门,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城市商业场所的典型样貌。
除了以上空间之外,还有很多种空间设置,形成一个整体的层叠状态,例如曼姐的理发店、四爷的锯木房、“荣门”惩罚违规者的“审判”场所,以及毕正明和“横一队”用来“练功”的废弃车厢等。空间的多元化设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把空间融入情节进程,而不是孤立、突兀地呈现出来。例如,放满人体模特的废弃车厢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从情节功能来看,是毕正明从学徒到“出师”的核心叙事空间,也是他和“横一队”相处逐渐融洽并推心置腹的地方,但这个车厢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的?不得而知。影片只用一个二宝开围栏铁锁的镜头交代了“大白桃”一行人破锁、登车,然后开始计时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这个独有的废弃空间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基本联系。毕正明在围江的容身之地,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刚到围江时在江边的废弃水泥建筑旁,毕正明做了一个搭塑料布的动作;后两次是夜晚的场景,“大白桃”教毕正明偷窃技巧。这两个场景第一次看时,很难看出是在哪儿,镜头只是聚焦两个人以及两个人略显暧昧的关系,对周围环境的呈现几乎为零。此外,影片中还两次出现了墓地的场景,毕正明被周队带着去祭奠牺牲的前辈:一次是毕正明受伤出院后,一次是反扒立功后,这两个场景的出现有点突兀,看不到其中的情节依据。总之,影片的空间设置虽然体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但如果脱离基本的情节支撑以及人物的行为逻辑,就会显得空间的有序性不够,导致堆砌、层叠的视觉效果。
正如影片的英文名The Return of The Lame Hero所提示的,这部电影在情节模式上确实是“英雄归来”的主题——从英雄受难到英雄出击,再到英雄的自我证明,构成基本的情节逻辑。影片的开局便是困局,志在反扒的警校毕业生毕正明上班第一天,人生就从高光时刻骤降到暗黑谷底,作为反扒警察的他却被扒手挑断脚筋,一夜之间从意气风发的警校人才变为持证的残疾人。“抓尽天下贼人”的理想眼看就要付诸东流。不甘失败的毕正明就此踏上证明正道的反扒之路,直到打入“荣门”“横一队”做卧底,并趁“英雄会”召开之际,配合警方将“荣门”各队一网打尽,毕正明作为一名普通警员所体现的执着与坚韧无疑是英雄成长主题的典型叙事模式。
随着影片的情节进展到后半段,英雄归来的情节主线越来越模糊:“荣门”的内讧此起彼伏,“花手”与四爷、少爷、“大白桃”打了个遍,同擅自登车行窃的“荣门”之外的帮派也展开血战;同时,毕正明和“大白桃”的感情线也开始变得抢眼。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主题表达的力度。当然,并不是说英雄归来的情节主线容不下一条情感副线或者多条内讧副线,关键是这些副线得经得起推敲,尤其是这条情感线,设置得模糊且牵强,不具备说服力。毕正明缘何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大白桃”成功“策反”?这个关键的转折性事件对于毕正明和“大白桃”双方而言,都应该有充分的心理铺垫,才能凸显人物性格并增加主题的力度以及人性深度,佐证毕正明寻正名、走正道的时间进程,而不是有突兀的跳跃感。“时间是连接事件的主轴,事件与事件之间在时间上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线性运动,尤其是离别与归来,人世的兴衰,追寻的历程等主题。”[2]而且,虽然“大白桃”的几句台词和两次行善行动与她的身份形成对照,“不偷老弱”“多积点德,没有坏处”,但这些行为的突发性使其游离在“大白桃”的行动体系之外,略显突兀。
除了突兀的感情线使得叙事主线被削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毕正明所面对的来自“荣门”的阻力也被消解了。四叔以及少爷作为“荣门”的重要人物,一直周旋在与“花手”的内讧中,“花手”作为四爷的关门弟子,为“荣门”打杂而未曾被接纳,就连他的身份也是很碎片化的,一会儿说小时候父母出了车祸,手没有接好;一会儿又从少爷口中得知“花手”的父亲是为“荣门”而死,真相一直悬浮不定。毕正明在“横一队”当卧底,面对的险境也很有限。这样一来,之间的对决张力就显得不充分,这必然会使得英雄归来的情节主线被弱化,且整个故事主题也失焦。这一系列叙事链条使得英雄自证的艰辛这一主线被弱化了,最终,英雄归来那一刻的主力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关注度难免会随着主题的失焦而被分散。
需要说明的是,与情节主线的弱化相比,影片对非英雄人物的处理是有深意的。影片中“荣门”大小扒手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核心人物四爷以及前任掌门曼姐、继任掌门少爷,身份即名字。如果说重量级人物的名字被隐去,是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倒也合乎常理。但整个盗窃团伙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没有名字,仅仅是作为遍布全国的“三横五纵”八个分队的队员而存在,这种整体的“无名”化处理为影片赋予了一层荒诞色彩和讽刺意味。影片中“荣门”的三方力量彼此水火不容,是盗窃集团内讧的缩影:“少爷”地位最高,介于四叔和其他队伍之间,想要接替四爷当新的掌门人,但每次出场总是生抢硬夺,有勇无谋;“大白桃”带领的江米条和二宝组成“横一队”,同样没有真实姓名;后来加入的毕正明作为新人“瘸子”,负责打入内部上英雄会,实现自己“抓尽天下贼人”的理想,同时撬动“横一队”的真善美,为同是受害者的无名者增加一层“贼道中的正道”之复杂色彩。四爷的关门弟子“花手”带领的“鬼队”处境最为尴尬,倚仗“荣门”却始终不得信任,既无法获得登上“161次列车”行窃的许可证,更无法实现想要的基本公平。“鬼队”的每次行动都名不正言不顺,前功尽弃,沦为一则笑话。但是影片结尾,“花手”最终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他在和毕正明的终极对战中听到“林乐华”这三个字,似乎遇到久违的自己,无奈而释然。作为“花手”,他与毕正明是之间的对决,是正道胜出后的受罚者;作为“林乐华”,他面对的是曾经真实的自己,是对生命历程中过往记忆和身份的追念。这种追念不仅包括曾经是电子琴比赛冠军的青春时光,还包括多年前在列车座位底下接到童年毕正明递来的汽水。
影片一开始就体现出叙事节奏的独特之处。镜头密度高、剪辑速度快,通过满溢的画面信息呈现站台拥挤的人流、候车室的不同角落,以及白天夜间、车下车上偷钱、偷东西、偷小孩的各种扒窃画面,节奏飞快,以至于会产生一种眩晕感,但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集中交代时代氛围、故事主题和主要人物,场景多、动作密、配乐快,不失为一种风格鲜明的耀眼开场。按理说,这作为一部影片的开始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从整体的时间规划上来说,短小精悍的开片也更容易为后续的情节进程留足时间和空间。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似乎并未感觉到影片在叙事节奏上的精细把控,没有张弛有度的合理安排,也缺乏适当的留白,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影片开场的快节奏一路蔓延、飞舞,没有基本的停顿和必要的沉淀。观影情绪被席卷在各方打斗的动作场景中,没有节奏放缓后的喘息和沉淀,共情能力自然也就会降低,尤其是对于关键事件的认同感。
围绕主要人物毕正明和“大白桃”的情节设置中,两个人身份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整部影片情节逻辑的合理性。毕正明养伤结束后从莱庆到围江,设法打入“荣门”,第一步就是遇到“横一队”,制造偶遇、追随、相救的机会,最终得到“大白桃”的信任,“大白桃”对毕正明的身份是否有过怀疑?按照情节来看,除了毕正明剪发后“大白桃”的表情有一丝诧异,并未有其他暗示,但是影片结尾却出现了“大白桃”精心藏起的学生证,这似乎在暗示什么,所以,在毕正明身份转变的这个情节链条上,逻辑有点断裂。另一个关键事件是“大白桃”的身份转变,一个多年的“荣门”成员从贼人转变为良人,从常理来看应该有一个矛盾挣扎的心理过程,但是影片并没有呈现这种转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只是一场夜晚的哭戏便了事,随后就是第二天走出坚定的、带有反转意味的步伐。这样的处理未免太过简单,在行为逻辑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同时也削弱了角色本身的厚重感。
影片的叙事节奏还体现在特写镜头的频繁使用以及快速切换上,尤其是人物的面部特写。如果说从开始的小孩哭脸经由毕业证盖戳,过渡到毕正明身着警服的面部特写是合乎逻辑的节奏;那么,在毕正明和周队的对话中,轮番切换两人的表情,人均五个面部大特写,而且周队还顶着一头假得不能再假的长发造型。“特写镜头将脸置于前景,使屏幕的表面变成了脸的表面,脸似乎转化为巨大的形象悬浮在观众眼前,让其物质的材质、细节以极其强烈的方式、放大的方式作用于观众的感官和身体”。[3]
这种镜头处理方式偶尔为之可增加适度的滑稽感,但在影片中密集出现会造成意义不明的面孔“悬浮”,甚至消解了本应有的反扒工作的严肃性和秩序感。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会发现,这种特写镜头出现的频率在不断上升。毕正明在天桥与小偷打斗的过程也是身体的局部和动作的特写,从视觉体验来看缺乏应该有的连贯性,以及双方力量的反转,只是硬性的打斗场面;之后在火车站与算命先生的对话,也是面部特写镜头的切换;就连毕正明办完残疾证,迎面碰上坐轮椅的男子时顺手扶了一下,也要切一个轮椅男的面部特写镜头。当然,不是说这些场景不能用特写镜头,但是如此高频率且没有区别地使用,最终削弱的是角色本身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毕竟,个体在任何一个情境中,面对任何处境都不会仅仅是面部表情的变化。人是环境中的人,将人置于环境中去呈现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核心事件的快速跳跃以及密集的特写镜头之外,影片中的人物塑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节奏很快,情绪和动作无限堆积,基本的过程被压缩,逻辑被忽略,难以产生共情。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留白,人物身上的悲情与无奈一闪而过。例如,江米条和二宝是被拐卖的儿童,本身是受害者,这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揭开这一真相的方式则显得太过仓促。两人本来在菜市场的二层教毕正明辨别楼下的有钱人。有一刻,他们顺着毕正明所指的方向看到一个和儿童搭话的男子,于是第一时间就认出是当初贩卖两人的人贩子。这种精准辨认的偶然性虽然是存在的,但按常理来说,多年过后隔着一层楼的距离,在人头攒动的公共空间中一眼辨认出人贩子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同样,毕正明在母亲的服装店守株待兔抓小偷以及追到天桥打斗的环节,也是以快节奏的动作切换为主,呈现打斗本身的激烈性。毕正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直接到了反扒办公室,汇报抓贼实绩,请求入列。


@HASHKFK